——與劉醒龍、黃建新談文學與電影領域的現實主義表達

1990年代初,黃建新意識到市場電影和藝術電影是有區別的。只有讓中國電影大規模化發展,讓更活躍的人去推動電影市場,才是良性的狀態。在此之后,他拍攝了電影《站直啰,別趴下》。圖為《站直啰,別趴下》劇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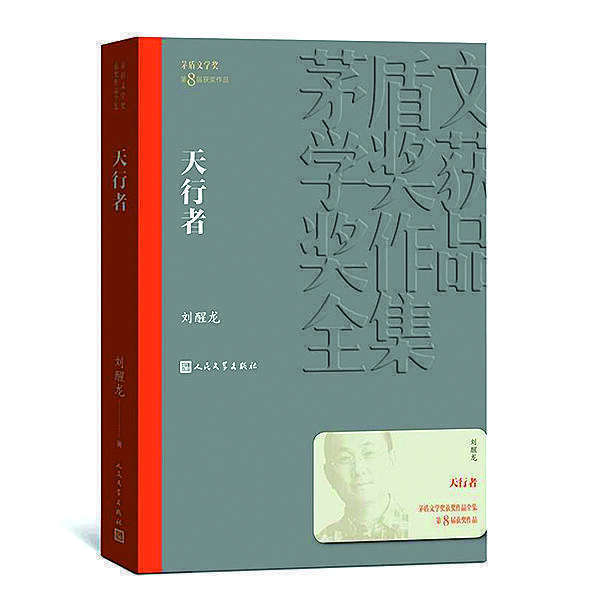
《天行者》劉醒龍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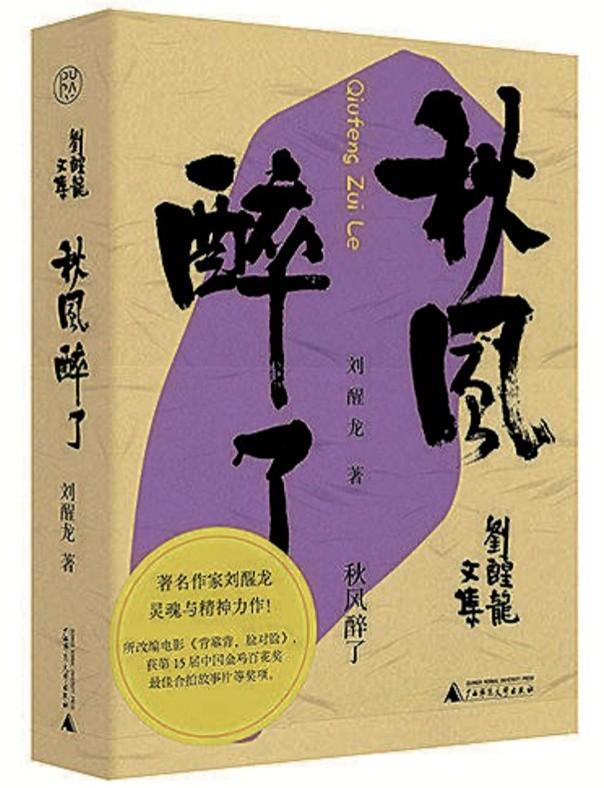
《秋風醉了》劉醒龍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電影與文學,都是研究現實與人生的藝術。如何以現實為基底進行藝術創作,如何塑造讓人共鳴的藝術形象,如何平衡虛構與現實的關系,是電影和文學共同探索的問題。所以,不管在小說還是電影領域,“現實主義”都不是新鮮話題,甚至是老生常談。但如何能真正做好“現實主義”,又一直是創作者面臨的“難題”。中國電影需要現實主義,所以會向小說“借力”,但中國電影市場還需要觀眾與票房,需要新的美學形式。這三者本不矛盾,若處理不好,則會呈現出一種割裂性,這在當下電影中也屢見不鮮。
不久之前,在北京電影學院北影大講堂“文學與電影”第二期巔峰對談活動中,著名導演黃建新與著名作家劉醒龍就此展開交流,共同探討小說與電影創作中現實主義的邊界與維度。
本報獲得授權,對此次對談進行獨家整理與刊發,以饗讀者。
——編者
嘉賓:黃建新 著名導演、編劇、制片人,金雞獎最佳導演
劉醒龍 著名作家,魯迅文學獎與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主持:劉小磊 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副教授
現實與虛構之間——從小說到電影
劉小磊:《背靠背,臉對臉》是改編自劉醒龍老師在1990年代的一部中篇小說《秋風醉了》。《秋風醉了》和《菩提醉了》《清流醉了》一同構成了您的文化館系列小說。小說故事生動得幾乎像現實搬演。您認為小說和現實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
劉醒龍:在文學界有一個行話,對現實主義品格的文學作品稱之為“正面強攻”。這是一個軍事上的術語,軍事“正面強攻”是最難的。在文學創作中,現實主義作品是最難的。我們對于現實很熟悉,但實際上未必人人都能理解。小說和現實的關系,我覺得首先是精神和靈魂的一種交流。我們生活在現實當中,我們自然了解現實,理解現實,甚至我們就是自己創造現實的人,為什么還需要小說呢?就是因為人和現實之間還是需要有一種東西進行溝通,這個東西包括小說、詩歌、散文,也包括電影。
劉小磊:黃建新導演最初是怎么發現這部小說的?您從《黑炮事件》開始,大部分作品都是由小說改編而來的,作品在詼諧呈現的同時,都有著直面現實的力量。您選擇小說進行改編的標準是什么?
黃建新:這部小說是在寧夏的時候,我正在拍《五魁》,有一天我的聯合導演楊亞洲在現場拿了一本《小說月報》給我,讓我看另外一部小說。我看了,寫得很好,但是沒有讓我那么著迷,我就往后翻,緊接著就是《秋風醉了》。我大概看了三分之一,就說“亞洲,趕緊找,這個在哪里”。看的時候我有特別多的聯想,有感觸,這是最直接的。
我自己拍的電影大量都來源于小說。因為我大學是中文系的,喜歡看小說。小說比電影帶來更多的聯想空間。電影只提供一個具象的東西,觀眾總會順著你營造的事物走,而消除了自己的空間聯想。同時,一百個人有一百個聯想,你的電影能不能說服觀眾就很重要。所以電影的二度創作能否把有深度的小說轉化為真正具有魅力的電影作品,是很有挑戰性的。
電影史上比較好的電影其實大都來自小說。作家不同于導演和編劇,因為編劇創作劇本幾乎不能完全進入個人的創作狀態,會有很多外部條件的干預,而作家不同。小說能提供更豐富的東西,這是電影的精神源泉。
劉小磊:醒龍老師很擅長寫中國式的人際交往,各式各樣的圓滑處事非常有經驗,或柔或剛,弦外之音,都處理得有聲有色,而且小人物的性格鮮明,像王副館長、老馬、小閆等等。這種生動的人物處理方式,在經驗和虛構之間,您是怎么處理的?您在觀察和塑造人物方面有沒有什么獨特的創作經驗?
劉醒龍:我的小說中一向有一種自己風格的堅持。大家在關注作品時往往最關注主要人物,就像《秋風醉了》里面的王副館長,忽略了次要人物。而我的小說里,次要人物寫得好不好關乎作品的成敗。你跟著主要人物走不大可能失誤,失誤的、有缺陷的往往是次要人物。一個作品的魅力也是次要人物烘托起來的。小說寫作領域里面有一句行話“小說的藝術就是閑筆的藝術”,看你閑筆寫得好不好。好的閑筆砍掉了,作品的光芒光輝、風格風采就消失了,這就是好的閑筆。小說的閑筆,決定這個作品的高下。我一直最努力寫的是小說里的次要人物,甚至是特別次要的人物。有些細節是至關重要的,讓這個作品有血有肉,否則就是骨架。
劉小磊:還想聊一下您筆下的父親形象。您曾經刻畫了非常多的父親形象,大多勤勞樸實、隱忍節儉,他們也會有一些劣根性,但也能被讀者理解。像《秋風醉了》里的王雙立的父親,雖然一心想要孫子,但是真聽說兒媳婦懷孕了,他要回鄉養豬給娘倆兒補身子用。面對小閆拿來的高級皮鞋,他確實不知怎么的,沒用力鞋子就破了,他還因此痛心和自責。您對于父親、父輩的描述,基于怎樣的態度和現實考量?
劉醒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中國的文化界,甚至是整個的文化界,彌漫著“審父情結”,就是對父輩的批判和重新審視。這是從西方哲學引進來的。我也有過。在我的內心,像《大別山之謎》這種先鋒色彩的作品里面,父輩的形象確實不是很好,對父輩帶著一種審視的眼光去看。隨著年齡的增長、生活閱歷的增加,我發現這里面有很大的問題,所以寫作風格就慢慢調整過來了。
劉小磊:但黃導在改編后,父親形象會變得更加尖刻和厲害。他看似沉默,主動幫人修鞋,也能夠隱忍。但實際他是有自己的狡黠和心機的。他想懲罰小閆,所以借機戳破了皮鞋,大鬧之后到醫院賣血。這讓電影的尖銳性變得更強了,也讓電影顯得更具有城市性的特征。您是如何理解1990年代的父輩形象的?在當時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您是怎么處理那種諷刺性和批判性的?
黃建新:其實我想表現的是改革開放初期,在一些事情上表現出來的對立狀態,比如《站直啰,別趴下》《背靠背,臉對臉》《紅燈停,綠燈行》,都是講這樣的一種狀態。《背靠背,臉對臉》中,局長一直不讓王雙立當館長,但是一退休,那個局長是個非常可愛的老人。有的時候,人的好壞,不是簡單的權力利益化的問題,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所以這三部故事,都是以群像為主體的。這個就特別逼近我們的生活狀態。我們的生活經常是這樣的,各個層次、各個年齡、男女老少,構成了我們生活所沉浸的一個圈。這三部電影就是想表達這種沉浸。
其實涉獵到心理層面上的意識,有一種叫“集體無意識”。我希望能夠通過電影,表現存在在心理上的問題,能夠警醒我們。人變得單純,是一個最難的事,但這是我們的理想,我們希望人能夠透亮、歡快、單純。可其實,司空見慣,甚至不以為然的事情,往往也是非常嚴重的事情。這就是當時處理父親那個人物時大概的想法。進一步講,中國文化中的人際關系是極為微妙的,一生也弄不明白,但想躲又躲不了,這就是現實。所以,每個人都希望用堅定的毅力和追求來保持自己完整的人性,這也構成了中國人生命的特點。
轉型與創新之間——現實主義的當下性
劉小磊:兩位老師在1990年代都有過一次重要的創作轉型。醒龍老師現在是當代現實主義創作的代表性作家,但最開始您在1980年代創作《大別山之謎》時,是非常先鋒的風格。您是怎么從當時最時髦的先鋒文學創作,轉向了對現實的關注?
劉醒龍:有很多契機,但最重要的還是人生的閱歷和寫作的體驗,以及個人在藝術修養上的慢慢積累。日常生活當中,我們作為孩子最不喜歡誰?是父母,他們是最愛你的人,最心疼你的人,給了你生命,但你最不喜歡他們,為什么?因為他們會給你責任,跟你嘮叨,批評你。文學也是這樣。現實主義就像父母,你特別了解他,就一點兒神秘性都沒有。但像其他風格,魔幻的、先鋒的,很容易玩出技巧來,那個東西就特別吸引人。但慢慢的,你會發現,現實主義是人生的主流,也是藝術的主流,也正是因為如此,主流就最容易被忽略。后來當我認識到現實主義是最重要的品格時,就認準了這條路,一直走下來。
劉小磊:黃導其實也是如此。《黑炮事件》到《錯位》《輪回》都是比較先鋒的創作風格,但到了《站直啰,別趴下》,視聽鋒芒感消失了,情節處理也更偏向溫和和喜劇的現實主義創作表達。為什么做了這樣改變?
黃建新:1980年代,不光是電影,小說、繪畫、詩歌、戲劇等,都開始出現新浪潮。在學校,同學們都讀尼采、弗洛伊德,似乎我們可以看全世界,大家都在如饑似渴地看,探索各種藝術形式的可能性。標新立異就是當時最沖動的想法,所以《黑炮事件》《錯位》都是在這個時期創作出來的。但是到了1990年代初,中國電影票房一年只有不到八億了,電影沒人看了。電影制片廠的領導都需要借錢發工資,那是電影特別低迷的時期。
我們在學校念書時,學校教給我們“電影是大眾的,喜聞樂見的藝術”。這對我是有影響的。1990年代初,我去澳大利亞做了一年多的訪問學者,去參加電影節,我意識到市場電影和藝術電影是有區別的。我們要讓中國電影有大的規模化發展,有更活躍的人去推動電影市場,這才更需要探索,只有這樣,才是良性的狀態。從澳大利亞回來后,我就拍了《站直啰,別趴下》。
劉小磊:醒龍老師是非常勤奮的作家,尤其在2000年后,從自己擅長的中短篇領域,開始往長篇小說進軍,像《天行者》《圣天門口》都取得了非常高的榮譽和肯定。請問保持這種持續創作的動力源泉是什么?當生活的一切變得更加穩定后,創作思路會逐漸固定和局限嗎?
劉醒龍:從2000年到現在,世界變化之巨大,不可思議。但是,在不可思議當中,我還是對人本身表示堅定的信心。必須對人自身有信心,才能獲得幸福感。人和萬物不一樣,就在于人是徹底的感情動物,是徹底的抽象動物。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易變。包括AI,我不相信AI能統治世界,AI在藝術領域永遠比不上人。人的感情需求太復雜了,真的說不清楚。就像寫小說,1990年代末,突然之間長篇不流行了,沒人看了,出版社印的書賣不出去,不允許超過12萬字。人家說我的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但是我不寫了,為什么不寫?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寫中篇和短篇對我來說太容易了,不存在任何挑戰性。生命有限,要做點有意義的事。我們這一行做什么呢?于是我寫長篇,《圣天門口》寫了六年。后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我們永遠不要低估了讀者,文學創作,作者寫完最后一個字只是完成一半,接下來在印刷出版和傳播過程中是讀者說了算。我們千萬不要以為讀者就這個水平,讀者總是希望自己更進一步的。我覺得電影也是這樣。
劉小磊:現在創作群體是越來越趨向于年輕化的,想問一下,兩位老師作為出色的現實主義創作的前輩,你們認為現在搞創作的年輕人應該怎么處理所面對的現實瓶頸和虛構之間的關系呢?
劉醒龍:我絕對相信年輕人的藝術才華,但是會對他們的生活經驗打個問號。我們在藝術創作上最大的瓶頸,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講,還是閱歷。這個閱歷不是說在機關里、在單位里的那種日子,那只是很小的一面。有一句話叫“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未來的藝術家、未來的文學家需要的是非常慎重地去看待世界。
2021年的時候,我坐一艘漁船,隨著海南水上考古隊在南海待了半個月。四平方米的船艙里面睡兩個大男人,那也是對心理極限的一種挑戰。有一個小島叫“全富島”,我們前一天下午去那個島上的時候,島上還是光禿禿的。很小很小的島,全是沙灘。那個海灘生成的時間不到一百年,有記載的。我們第二天早上上那個島的時候,就發現那個島的中間有一個植物長起來了,很神奇的,它就是讓我們去見證。我們一定要作為生活的見證者,首先作為廣闊生活的見證者。我們一定不能離開生活,但是我們不能離開什么生活?我們不能離開廣大的社會生活,只有廣大的社會生活非常豐富的時候,才能讓你的作品豐富起來,從而變成偉大的作品。
黃建新:年輕人有年輕人的優勢,就是因為年輕,敢做敢沖,敢不按說的辦。當年我拍《黑炮事件》,那個大鐘表四分鐘不動的鏡頭,讓我重拍。我給西影廠的廠長吳天明打電話,他也正在外面拍戲。我說“我不想(重)拍”。他說“你確定你是真的有想法,不是照貓畫虎?”我說“我是一個體系,我確定有想法”。這就是年輕人。因此,指導年輕人應該怎么做,挺難的。因為是年輕人生活在當下,對當下生活的理解,年輕人比我們敏感。每一代都在變,這個變化是客觀存在的,否則時代就不前進了。看現在年輕人的語言,你會看到他們對喜劇的理解,對語言幽默感的理解跟以前是不一樣的。這就是變化,是語境的變化,是語境的變化帶來所有的變化,包括藝術也會變。這其實是年輕的優勢,我們也是這么過來的。
但是,和現在年輕人不同的是,當年我們都經歷了特別多生活中的事。比如醒龍老師,他在文化館經歷了很多的事,我們這代人都下過鄉,當過兵,經歷很多生活上的事情。這是現在的年輕人不具備的,所以希望大家把視野打開,多讀一些社科類的書,讀一些哲學的書,這對我們到了一定年齡,能夠比較洞徹地認識世界和分析事情是有好處的。我自己也是這么經歷過來的,當時覺得好多書讀不懂,沒啥用,但是很多年之后,遇到某件事情,突然把書翻出來再看,覺得非常有用。僅此而已。年輕人,大家努力往前沖就是了!

